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西夏文化
杜建錄 寧夏大學民族與(yu) 曆史學院院長、中華民族共同體(ti) 研究院院長,民族學一流學科負責人,民族學一級學科博士點負責人,“長江學者”特聘教授,全國“五一勞動獎章”獲得者,全國先進工作者,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範個(ge) 人,享受國務院政府特貼。主要從(cong) 事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、西夏曆史與(yu) 文獻研究。主持完成或在研國家和省部級課題20餘(yu) 項,其中國家社科重大2項、重點2項,在《民族研究》《中國史研究》等刊物發表論文140餘(yu) 篇,出版著作17部,其中《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研究》入選國家哲學社會(hui) 科學成果文庫,13項成果獲教育部和自治區優(you) 秀成果獎,其中一等獎5項。
宋遼夏金時期是我國曆史上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時期,當時的契丹、黨(dang) 項、女真和漢族長期交往交流交融,逐漸接受漢族傳(chuan) 統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。換言之,曆史上的遼、夏、金文化並不等於(yu) 契丹文化、黨(dang) 項文化和女真文化。沒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,就沒有西夏的建立和西夏文化的發展。
西夏文化的形成
建立西夏國的黨(dang) 項人是我國古代羌族的一支,長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東(dong) 部,南北朝時期就見於(yu) 史書(shu) 記載。隋唐之際,黨(dang) 項部落林立,“大者五千餘(yu) 騎,小者千餘(yu) 騎”。這些大大小小的黨(dang) 項部落以遊牧為(wei) 生,不知稼穡。沒有文字,但候草木以記歲時。平時“各為(wei) 生業(ye) ”,隻有對外戰爭(zheng) 時才相屯聚。
這一時期的黨(dang) 項,一度依附鮮卑吐穀渾,在長期的交往交流中,形成了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現象,以至於(yu) 唐宋時有人認為(wei) “吐穀渾者,今之文扶羌是也”。現代學者也指出,“鮮卑人羌化了,因之吐穀渾實際上是羌族國家”。說吐穀渾羌化了,就是吐穀渾大量吸收和融匯了羌族的文化與(yu) 血緣。同時,這種吸收與(yu) 融匯是雙向的,羌族也大量吸收了吐穀渾的文化與(yu) 血緣。經過曆史歲月的洗禮,到了北周、隋之際,今青海湖一帶的黨(dang) 項基本融匯到吐穀渾,他們(men) 在這一帶的活動就從(cong) 史書(shu) 中消失了。當然,其中也包含遷徙的原因。而鬆州一帶的吐穀渾則被黨(dang) 項所融合,有學者認為(wei) ,建立西夏王國的拓跋部,實際上是被羌化的鮮卑吐穀渾人,他們(men) 已與(yu) 黨(dang) 項羌沒有多大的區別,故兩(liang) 唐書(shu) 的作者及後世學者把他們(men) 看作黨(dang) 項羌。早期的黨(dang) 項正是在這種民族大融合中發展壯大起來的。
在曆史上,對黨(dang) 項社會(hui) 發展影響最大的是中原王朝,公元六世紀末期,隋朝統一中國,結束了長期的南北割據局麵,人民生活得到暫時的安定。585年,黨(dang) 項大首領拓跋寧叢(cong) 等各率部眾(zhong) 到旭州內(nei) 附,被隋文帝授為(wei) 大將軍(jun) 。596年,黨(dang) 項一度進攻會(hui) 州,被隋朝軍(jun) 隊打敗後,紛紛內(nei) 附,遣子弟入朝謝罪,表示“願為(wei) 臣妾”,“自是朝貢不絕”。
唐朝建立後,黨(dang) 項與(yu) 中原的關(guan) 係進一步得到加強,高祖武德年間,黨(dang) 項多次遣使朝貢。629年,黨(dang) 項酋長細封步賴舉(ju) 部內(nei) 附,太宗以其地為(wei) 軌州,拜步賴為(wei) 刺史。其他黨(dang) 項酋長聞風而動,“相次率部落皆來內(nei) 屬,請同編戶”。太宗厚加撫慰,列其地為(wei) 岷、奉、岩、遠四州,“各拜其首領為(wei) 刺史”。631年,太宗遣使開黨(dang) 項河曲地為(wei) 六十州,“內(nei) 附者三十四萬(wan) 口”。隻有最為(wei) 強盛的拓跋部沒有歸附,在唐朝的軍(jun) 事壓力和勸誘下,大首領拓跋赤辭也率眾(zhong) 歸附,唐太宗列其地為(wei) 懿、嵯、麟等三十二州,以鬆州為(wei) 都督府,任命拓跋赤辭為(wei) 西戎州都督,賜皇姓李。於(yu) 是,從(cong) 今青海積石山以東(dong) 的黨(dang) 項居地,全部列入了唐王朝的版圖,黨(dang) 項與(yu) 唐朝的關(guan) 係進一步密切。
黨(dang) 項歸附唐朝前後,從(cong) 青藏高原上崛起的吐蕃政權不斷向外擴張,征服吐穀渾,攻占大片黨(dang) 項居地。當時的黨(dang) 項麵臨(lin) 著重大選擇:或投附吐蕃,成為(wei) 吐蕃統治下的部落;或向唐朝內(nei) 地遷徙,成為(wei) 唐朝的部民。在唐朝羈縻懷柔政策的感召下,黨(dang) 項選擇了唐朝,逐水草向西北內(nei) 地遷徙。其中最為(wei) 強族的拓跋部比較完整地從(cong) 青藏高原東(dong) 部的鬆州遷徙到黃土高原東(dong) 部的慶州。“安史之亂(luan) ”後,又從(cong) 慶州遷往銀州以北、夏州以東(dong) 的平夏地區。
黨(dang) 項遷居的河隴地區,自漢代以來是漢族人民長期生活並創造著封建文明的所在,黨(dang) 項人在這裏定居下來,無論地理條件抑或曆史條件,對他們(men) 吸收漢族封建文明,發展生產(chan) 與(yu) 繁殖人口,都是極為(wei) 有利的,一部分黨(dang) 項人學會(hui) 了農(nong) 耕。當然唐代學會(hui) 農(nong) 耕的黨(dang) 項人數很少,他們(men) 大部分仍以傳(chuan) 統的畜牧為(wei) 生。
沈亞(ya) 之《夏平》指出:“夏之屬土廣長幾千裏,皆流沙,屬民皆雜虜,虜之多者曰黨(dang) 項,相聚為(wei) 落,於(yu) 野曰部落。其所業(ye) 無農(nong) 桑事,畜馬、牛、羊、駱駝。”
隨著生產(chan) 的發展和剩餘(yu) 產(chan) 品的增多,商品交換日益繁榮。黨(dang) 項人用自己的畜產(chan) 品和漢族人交換糧食、絲(si) 綢、武器和其他生活日用品。黨(dang) 項馬是最受中原歡迎的商品,唐代著名詩人元稹即有詩雲(yun) :“求珠駕滄海,采玉上荊衡,北買(mai) 黨(dang) 項馬,西擒吐蕃鸚。”929年,後唐莊宗閱蕃部進馬,樞密使安重誨奏曰:“吐渾、黨(dang) 項近日相次進馬,皆給還馬直,對見之時,別賜錦彩,計其所費,不啻倍價(jia) ,漸成損耗,不如止絕。”莊宗曰:“常苦馬不足,差綱遠市,今蕃官自來,何費之有?外蕃錫賜,中國常道,誠知損費,理不可止。”自是蕃部進馬不絕於(yu) 路。
內(nei) 遷黨(dang) 項中,拓跋部和中原王朝的聯係最為(wei) 密切。880年,黃巢農(nong) 民起義(yi) 軍(jun) 攻克都城長安。唐僖宗在奔蜀途中,詔令拓跋思恭率部鎮壓起義(yi) 軍(jun) 。拓跋思恭應詔率所部蕃漢軍(jun) 隊南下勤王,僖宗為(wei) 此特授思恭為(wei) 夏州節度使,複賜姓李,封夏國公。同年唐朝又贈夏州節度為(wei) 定難節度。從(cong) 此夏州地區獲得了定難軍(jun) 的稱號,統轄銀、夏、綏、宥四州之地,拓跋李氏成為(wei) 名副其實的地方藩鎮。
五代時期,黨(dang) 項拓跋部繼續和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關(guan) 係。913年,後梁封夏州節度使李仁福為(wei) 隴西郡王,按此為(wei) 夏州拓跋李氏封王之始。924年,後唐授李仁福為(wei) 檢校太師兼中書(shu) 令、夏州節度使,晉爵朔方王。951年,後周太祖封李彝殷為(wei) 隴西郡王,954年,又晉爵西平王。
960年正月,趙匡胤代周建宋,西平王李彝興(xing) 立即遣使入賀。962年,李彝興(xing) 入獻良馬300匹。宋太祖趙匡胤親(qin) 命工匠為(wei) 彝興(xing) 特製一個(ge) 玉帶,遣使回贈。967年,定難節度使李彝興(xing) 卒,宋太祖廢朝三天,贈太師,追封夏王。
980年,夏州節度使李繼筠卒,其弟李繼捧繼位後政局出現動蕩。宋太宗趁機遣中使持詔,令李繼捧攜家人入朝。隨後押解拓跋李氏緦麻以上親(qin) 族全部赴闕,夏州拓跋李氏政權一度中斷。
李繼捧族弟李繼遷不願離開“故土”,率數十名親(qin) 信逃往地斤澤,起兵抗宋,在黨(dang) 項豪族和契丹的支持下,逐漸強大起來。997年,宋真宗授李繼遷為(wei) 定難軍(jun) 節度使。李繼遷又進一步對外擴張,攻占靈州,易名西平府,將統治中心由夏州遷到靈州西平府。同時繼續向西發展,北收回鶻銳兵,西掠吐蕃健馬,經李德明、李元昊祖孫三代,最終占領河西諸郡,奠定西夏立國的版圖。
1003年12月,李繼遷和西涼吐蕃作戰時中流矢,次年因傷(shang) 重而死。其子德明繼位後和好宋朝,“貢奉之使,道路相屬”。這些使節除用馬匹換取宋朝的賞賜外,還“出入民間”,“市所須物”。民間兜售不出的“官為(wei) 收市”。每個(ge) 使團所獲利潤不下一二十萬(wan) 。1007年,應德明的請求,宋朝在保安軍(jun) 設置榷場,以繒帛、羅綺易駝馬、牛羊、玉、氈毯、甘草,以香藥、瓷漆器、薑桂等物易蜜蠟、麝臍、毛褐、羱羚角、硇砂、柴胡、蓯蓉、紅花、翎毛。非官市者,“聽與(yu) 民交易”。
黨(dang) 項內(nei) 遷後和中原漢族密切的政治經濟交往交流,必然帶來文化上的深度融合。夏州拓跋政權墓誌的形製和唐代官員貴族墓誌毫無二致,誌蓋篆書(shu) ,刹麵刻漢族傳(chuan) 統的八卦紋飾。進入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後,吸收借鑒漢族傳(chuan) 統文化的意願更加迫切,李繼遷“潛設中官,全異羌夷之體(ti) ;曲延儒士,漸行‘中國’之風”。李德明衣食住行,一如宋朝,正如宋人富弼所言:“拓跋自得靈夏以西,其間所生豪英,皆為(wei) 其用,得中國土地,役中國人力,稱中國位號,仿中國官屬,任中國賢才,讀中國書(shu) 籍,用中國車服,得中國法令,是二敵所為(wei) ,皆與(yu) 中國等。”這裏的“中國”是指漢族中原王朝,拓跋夏的位號、官屬、書(shu) 籍、車服、法令“皆與(yu) 中國等”,清楚地說明西夏建國前完全繼承了中原漢族的文化和製度。換言之,如果沒有和中原漢族的交往交流交融,就沒有黨(dang) 項社會(hui) 的發展,也沒有後來的西夏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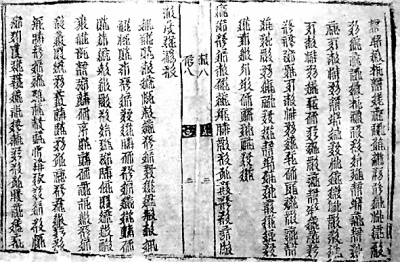
西夏文刻本《論語》。資料圖片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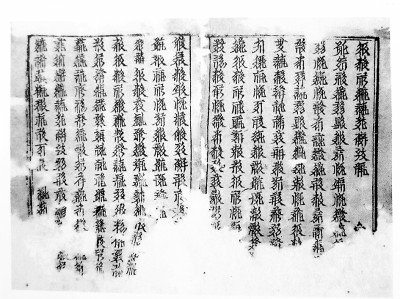
《番漢合時掌中珠》西夏文序。資料圖片
西夏文化的多樣雜糅
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西夏文化,雜糅了漢族文化、黨(dang) 項文化、吐蕃文化、鮮卑文化、回鶻文化等成分。中原漢族文化是西夏文化的核心,元昊稱帝建國前夕,仿照唐宋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官製,同時創製文字,建立蕃學,更定禮樂(le) ,禿發胡服,築壇受冊(ce) 。從(cong) 表象上看意在突出民族特點,但其本質仍脫離不了中原漢族文明。“裁禮之九拜為(wei) 三拜,革樂(le) 之五音為(wei) 一音”,隻是從(cong) 務實的角度精簡唐宋禮樂(le) ,而不是革去唐宋禮樂(le) 而用番樂(le) ,“正朔朝賀雜用唐宋典式”。文臣服飾為(wei) “襆頭、靴笏、紫衣、緋衣”,完全是唐宋官員服飾;武將服飾也繼承了傳(chuan) 統的等級製度;至於(yu) “民庶青綠,以別貴賤”,更是漢族傳(chuan) 統的製度。元昊禿發也隻限境內(nei) 的黨(dang) 項人,漢族仍是傳(chuan) 統的發式。
這一時期西夏文字的創製則完全借鑒和模仿了漢字。在字體(ti) 結構上,西夏文字和漢字一樣,有偏旁部首,基本筆畫也有漢字的點、橫、豎、撤、捺、提等,以致識漢字的人“乍視,字皆可識,熟視,無一字可識”。漢文和西夏文一樣,是西夏的通用文字,漢學教授漢文,蕃學教授番文(西夏文),出土的西夏公文,既有漢文也有西夏文。國家的法令也一樣,夏仁宗李仁孝頒行的《天盛改舊新定律令》有番文和漢文兩(liang) 種文本,目前隻保留下來番文文本。
西夏前期盛行漢傳(chuan) 佛教,統治者大興(xing) 土木,廣建寺院,翻譯從(cong) 宋朝請來的漢文《大藏經》。據統計,西夏前四朝共翻譯漢文佛經有三千多卷,這在我國古代佛經翻譯史上是少有的,從(cong) 而為(wei) 漢傳(chuan) 佛教的廣泛傳(chuan) 播與(yu) 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,也被西夏繼承下來。出土的西夏文獻中,有大量的道教文獻。西夏設有專(zhuan) 門管理道教事務的機構“道士功德司”。法律保護道觀、影像等道觀財產(chan) 。道士上層獲賜黃、黑、緋、紫服,犯罪後允許以官抵罪。西夏社會(hui) 流傳(chuan) 辟穀術,開國皇帝元昊子寧明練習(xi) 辟穀術時走火入魔,氣忤而死。西夏的占卜術包括道教的“五行卦”和“金錢卦”。
西夏宮廷音樂(le) 深受唐宋音樂(le) 影響,音節悠揚,“清厲頓挫”。民間音樂(le) 更受中原漢族的影響,北宋著名政治家沈括為(wei) 陝西邊帥時,曾作過十幾首歌,其中一首有“萬(wan) 裏羌人盡漢歌”之句,說明夏宋沿邊一帶的黨(dang) 項人都會(hui) 唱漢歌。另據宋人葉夢得記述,他在丹徒做地方官時,“嚐見一西夏歸明官雲(yun) :‘凡有井水飲處,即能歌柳詞’,言其傳(chuan) 之廣也”。柳永為(wei) 北宋著名詞人,他的詞作情意纏綿,大多譜上曲子在市民階層中廣為(wei) 流傳(chuan) ,也得到了西夏人民的喜愛。
西夏紀年采用我國古代傳(chuan) 統的年號紀年方式,皇帝新即位要改元,國家發生重大事件或革故鼎新也要改元,並鑄年號錢幣。皇帝在位時上尊號,去世後上廟號、諡號,陵墓有陵號。陵墓基本形製“仿鞏縣宋陵而作”,分別由角闕、鵲台、神牆、碑亭、外城、門闕、內(nei) 城、獻殿、塔狀靈台等部分組成,平麵布局大體(ti) 按照中原大建築群設計,強調中軸線左右對稱。
中原絲(si) 織品和衣物的輸入,改變了黨(dang) 項人單一的“衣皮毛”穿戴。1975年在銀川市西夏陵區一〇八號陪葬墓出土的素羅、紋羅、工字綾、異向綾和茂花閃色錦等各色絲(si) 織品殘片,就是當時從(cong) 中原輸入的。
黨(dang) 項人是西夏的主體(ti) 民族,內(nei) 遷後在接受漢文化的同時,依然保留了大量本民族的文化習(xi) 俗。早期黨(dang) 項人把不可抗拒的風雨雷電雪雹等自然現象統歸於(yu) “天”的支配,每三年一聚會(hui) ,殺牛羊以祭天。後來隨著社會(hui) 的發展,又產(chan) 生了鬼神崇拜和巫術迷信。在黨(dang) 項人的觀念裏神主善,鬼主惡。黨(dang) 項人居住的正室中留一間專(zhuan) 門供神。
巫的職責是驅鬼、咒鬼和占卜吉凶,人生病後召巫送鬼,或者移居他室以避病。對戰死者要“殺鬼招魂”。占卜之法有四,一是“炙勃焦”,用艾草燒羊胛骨,看其征兆;二是“擗算”,擗蓍草於(yu) 地以求數;三是“咒羊”,夜牽羊焚香禱告,次日晨殺羊,腸胃通則表示吉利,羊心有血則凶;四是“矢擊弦”,即用箭杆擊打弓弦,聽其聲音而占勝負和敵至之期。這些以羊和弓弦作為(wei) 工具的占卜行為(wei) ,帶有濃厚的遊牧民族色彩。
複仇是黨(dang) 項人又一重要舊俗,早期黨(dang) 項“尤重複仇,若仇人未得,必蓬頭垢麵,跣足蔬食,要斬仇人而後複常”。建國後依然“俗喜複仇”。如果仇解,用雞豬狗血和酒飲之,誓曰“若複報仇,穀麥不收,男女禿癩,六畜死,蛇入帳”。
早期黨(dang) 項人盛行收繼婚製,“妻其庶母及伯叔母、嫂、子弟之婦”。建國後在漢文化的影響下,開始明媒正娶和買(mai) 賣婚姻。締結婚姻一般要經過訂親(qin) 、納聘禮、置辦嫁妝、娶親(qin) 四個(ge) 環節,當然,和漢族相比,黨(dang) 項青年男女之間的戀愛與(yu) 婚姻是比較自由的,家庭一般不會(hui) 幹預他們(men) 暗中約會(hui) 。
西夏時期的黨(dang) 項文化最重要的表現是創製文字,並在全國推廣使用。元代以後隨著黨(dang) 項民族的融合,西夏文字也逐漸不為(wei) 世人所識,使這種文字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。其實西夏文創製並不神秘,在我國多民族曆史發展過程中,當一個(ge) 民族經濟社會(hui) 發展到一定的階段,就開始創製本民族文字,如回鶻文、吐蕃文、契丹文、女真文、蒙古文、滿文等。
西夏境內(nei) 有大量吐蕃人,西夏文化包含著濃鬱的吐蕃文化成分,吐蕃語不僅(jin) 在吐蕃人群中使用,而且和黨(dang) 項語、漢語共同構成西夏的佛教用語。天盛年間頒布的法律明文規定:番(黨(dang) 項)、漢、吐蕃三族人都可以任僧官,但必須會(hui) 念誦十四種經咒,其中藏文經咒要占半數。
西夏前期主要奉行漢傳(chuan) 佛教,中後期藏傳(chuan) 佛教大量傳(chuan) 到河西地區,到李仁孝時,已在全國很有影響。西夏在中央機構中,設立專(zhuan) 門管理漢傳(chuan) 佛教和藏傳(chuan) 佛教的機構,來自吐蕃的高僧出任西夏國師和帝師。流傳(chuan) 下來的西夏繪畫藝術,大量是密教藝術。
西夏軍(jun) 隊以“抄”為(wei) 最小單位,由正軍(jun) 和負擔組成的“抄”,脫胎於(yu) 吐蕃的“組”,負擔等於(yu) 吐蕃時代的“仆役”。吐蕃的曆法也傳(chuan) 到了西夏,二十世紀70年代在甘肅武威下西溝峴出土的西夏文會(hui) 款單,稱1194年為(wei) “天慶虎年”。這種把十二生肖與(yu) 五行結合,再配以陰陽的紀年方法,無疑是受藏曆的影響。
黨(dang) 項與(yu) 吐蕃經過數百年的交往交流,形成了水乳交融的關(guan) 係,留居青藏高原以及河、湟、洮、岷的黨(dang) 項吐蕃化了,進入西北沿邊的吐蕃則有明顯的黨(dang) 項化趨勢,即使沒有黨(dang) 項化,也已經是“風俗相類”了,所以當時的宋朝中原人有時也分不清哪些是吐蕃,哪些是黨(dang) 項,往往通稱其為(wei) “蕃部”。
甘州回鶻歸附西夏後,長期生活在河西走廊,繼續使用本民族文字,現存西夏時期的回鶻文文獻有寫(xie) 本、刻本和活字本。元人馬祖常《河西歌》曰:“賀蘭(lan) 山下河西地,女郎十八梳高髻”。“高髻”為(wei) 回鶻婦女的發式,反映出回鶻社會(hui) 風俗對西夏社會(hui) 生活的滲透。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西夏洞窟壁畫中,有許多回鶻人的形象。
夏遼為(wei) 盟國,在政治上貢使往來不斷,遼朝三次將公主遠嫁西夏,在經濟上又於(yu) 沿邊辟有榷場,密切的政治、經濟往來,必然會(hui) 帶來文化上的交流。契丹的“射鬼箭”習(xi) 俗和西夏的“殺鬼招魂”習(xi) 俗,存在著相互影響或同源異流的關(guan) 係。西夏男子禿發與(yu) 鮮卑、契丹的禿發也存在一定的淵源關(guan) 係。
金朝建立後,西夏與(yu) 之關(guan) 係非常密切,由於(yu) 女真入主中原後很快漢化,因此由金朝輸入西夏的文化大多是漢文化。如1154年西夏使金謝恩,“且請市儒、釋書(shu) ”。另外,內(nei) 蒙古黑水古城曾發現《劉知遠諸宮調》,說明金朝的諸宮調也傳(chuan) 入西夏。
西夏文化中的儒家文化
黨(dang) 項進入西北後三百多年的民族融合,特別是拓跋夏政權進入河套平原與(yu) 河西走廊後,逐漸接受中原漢族的政治製度,元昊稱帝建國前夕,仿照唐宋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官製。“其官分文武班,曰中書(shu) 、曰樞密、曰三司、曰禦史台,曰開封府,曰翊衛司、曰官計司、曰受納司、曰農(nong) 田司、曰群牧司、曰飛龍院、曰磨勘司、曰文思院、曰蕃學、曰漢學。”除蕃學外,這些官職機構無論從(cong) 名稱上,還是從(cong) 職掌上,都是仿照中原宋朝製度,甚至連“開封府”這樣地域性很強的職官也都照搬過來。夏仁宗李仁孝統治時期,隨著西夏封建政權的進一步鞏固和經濟文化的發展,官製也更加完備。從(cong) 西夏文法典《天盛改舊新定律令》來看,當時西夏政府機構分為(wei) 上、次、中、下、末五等。至此,西夏職官製度之完備、品級之係統,已和中原相差無幾。
官吏選任方麵,西夏除保留部落社會(hui) 的世襲製外,廣泛吸收了中原漢族的恩蔭、察舉(ju) 、科舉(ju) 、銓選等製度。《宋史·夏國傳(chuan) 》記載,1147年仁宗“策舉(ju) 人,始立唱名法”。這是史書(shu) 最早關(guan) 於(yu) 西夏科舉(ju) 取士的記載。西夏的科舉(ju) 分番漢兩(liang) 種,番科考西夏文儒經,漢科考漢文儒經,所謂“番科經賦與(yu) 漢等,特文字異耳”。西夏後期許多名臣政要乃至國主都是通過科舉(ju) 考試發達的。第八代皇帝神宗李遵頊,“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,為(wei) 大都督府主”。夏神宗時吏部尚書(shu) 權鼎雄亦是進士出身。夏末名臣高智耀“登本國進士第,夏亡,隱賀蘭(lan) 山”。
將儒家思想植入法律。這是西夏以儒治國的最重要體(ti) 現。夏仁宗天盛年間頒行的《天盛改舊新定律令》以儒家思想為(wei) 指導,把維護君權、父權、夫權作為(wei) 根本任務,開篇首列謀逆、失孝德禮、背叛、惡毒、不道、大不恭、不孝順、不睦、失義(yi) 、內(nei) 亂(luan) 等“十惡”罪,完全和唐宋立法指導思想一致。犯“十惡”罪一律不赦,也“一律不允以官當”。除“十惡”不赦外,其他犯罪按照“刑不上大夫”的禮教,照搬唐宋律中的“八議”(議親(qin) 、議故、議賢、議能、議功、議貴、議勤、議賓)及相應的請、減、免、罰等製度。
西夏法律維護皇帝(國主)至高無上的地位,規定黃色是皇帝專(zhuan) 用顏色,龍鳳是帝後專(zhuan) 用圖案,任何人都不得僭越。皇帝的人身安全和權威尊嚴(yan) 神聖不可侵犯,除因公奉旨帶刀劍、弓箭、鐵杖等武器外,不許諸人隨意帶武器來內(nei) 宮。
西夏也繼承“父為(wei) 子隱,子為(wei) 父隱”的儒家禮法,除謀逆、失孝德禮、背叛等三種情況可以舉(ju) 告外,其他一般犯罪,不許舉(ju) 告。同時對窩藏、包庇犯罪的親(qin) 屬減免刑罰。子女不經父母同意不得擅自另立門戶。儒家的德主刑輔、明德慎刑、矜恤老弱疾病原則亦為(wei) 西夏法製所承襲,對老耄、幼弱、殘疾、侏儒、重病者犯罪,在量刑和服刑方麵給予適當優(you) 待,對監禁期間染有疾病的囚犯積極治療或保外就醫。
西夏儒家政治製度的推進,離不開學校教育。元昊設立蕃學、漢學,蕃學所用課本除自編的番文讀本外,還有譯自漢文的《孝經》《爾雅》《四言雜字》等。漢學主要教授漢文啟蒙讀本和儒家經典。目前還不清楚西夏立國初期是否在蕃學教授漢文,但有一點是肯定的,即最初的蕃學教授大多是通漢文的讀書(shu) 人,番文本身就是仿照漢字創製的,推行番文的元昊就“通蕃漢文”。元昊之後,西夏一度陷入蕃禮漢禮之爭(zheng) ,“蕃禮”是用黨(dang) 項族的禮製協調統治秩序,“漢禮”是用中原漢族的禮儀(yi) 和製度規範統治秩序。經過長期的鬥爭(zheng) ,到崇宗李乾順和仁宗李仁孝在位時,“漢禮”最終取得勝利。1101年,夏崇宗建立國學,設弟子員三百,以廩食之。仁宗即位後,進一步推進漢學教育。1144年,在皇宮內(nei) 建立小學,凡宗室子孫7歲至15歲都可以入學。同時令州縣立學校,弟子員增至三千人。第二年,又建大漢太學,仁宗親(qin) 臨(lin) 太學祭奠先聖先師孔子。1146年,尊孔子為(wei) 文宣帝,這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尊孔為(wei) 帝。
這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,同時代的宋儒以複興(xing) 儒學至尊地位為(wei) 己任,湧現出荊公新學、二程洛學、蘇氏蘇學諸學派著書(shu) 立說,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,儒家學說的發展達到一個(ge) 新的高峰。而同期的西夏仍處於(yu) 對儒經的學習(xi) 和一般性的譯注階段,遠沒有達到創新和發展的程度。但我們(men) 仍不能因此低估西夏以儒治國的意義(yi) ,作為(wei) 一個(ge) 由黨(dang) 項人建立的多民族政權,它積極吸收中原漢族文化,官僚體(ti) 製效仿唐宋,主流意識形態崇尚儒學漢禮,從(cong) 中華民族共同體(ti) 發展史來看,這具有深遠的曆史進步意義(yi) 。
結語
宋遼夏金時期是我國北方民族社會(hui) 形態重大轉折時期。
此前,無論秦漢之匈奴,抑或隋唐之突厥,都是部落製下的遊牧社會(hui) ,遊牧文化和農(nong) 耕文化在河套到河西走廊一帶處於(yu) 長期的“拉鋸”狀態:中原王朝強大時,北逐匈奴,移民河套與(yu) 河西走廊,農(nong) 耕文化占主導地位;中原王朝衰微時,北方民族進入該地區,遊牧文化占主導地位。“拉鋸”狀態下,農(nong) 耕文化和遊牧文化在這一地區交往交流交融相對緩慢。
進入宋遼夏金時期後,這種情況發生了急遽變化,無論契丹建立的遼朝,還是黨(dang) 項建立的西夏以及女真建立的金朝,都是包括漢族在內(nei) 的多民族政權,其文化在多樣雜糅的基礎上,占主導地位的是中華傳(chuan) 統文化,最有意義(yi) 的是,三個(ge) 政權都自認為(wei) 是中國而非夷狄。這種文化上的認同,是曆史上中華民族共同體(ti) 的重要體(ti) 現,值得我們(men) 進一步深入探討。
版權聲明:凡注明“來源:新利平台”或“新利平台文”的所有作品,版權歸高原(北京)文化傳(chuan) 播有限公司。任何媒體(ti) 轉載、摘編、引用,須注明來源新利平台和署著作者名,否則將追究相關(guan) 法律責任。
 新利平台微博
新利平台微博 新利平台微信
新利平台微信




